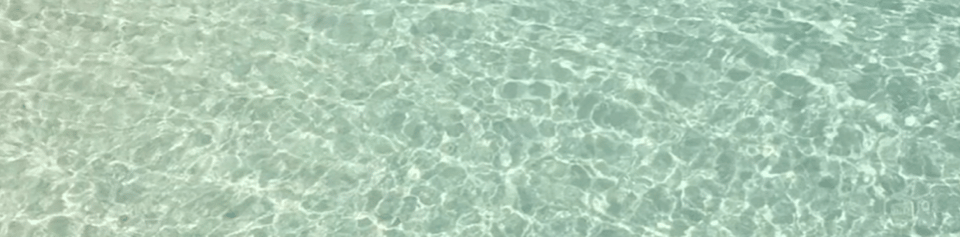2025 年 9 月 28 日,当北京女足的球员们捧起奖杯的时刻,先农坛体育场看台上的欢呼声或许暂时打破了球队在中国女足顶级联赛中长达 23 年的沉寂。
在这之前的五年,创造女超联赛五连冠纪录的武汉女足一直站在金字塔尖。它的崛起故事印证着世界足球领域的一种常见逻辑:集中对这个行业而言最重要的资源──球员。最多时,有 8 名国脚在此效力。直到 2024 年,足协开始推行限薪限投、限制国脚过度集中的政策,改变联赛“一家独大”的局面。
北京女足的冠军故事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2015 年,女足开始职业化,与武汉等迅速拥抱潮流、改组俱乐部的球队不同,北京女足一直站在体制与市场的中间地带。尽管在两年后与投资方北控集团签约,作为俱乐部参赛,它仍是市体育局下属的队伍。这也使它在 2021 年赞助商撤资之后的 3 年间,免于遭遇球队撤资后的普遍命运──欠薪、降级、解散。
在剧烈的变化中,北京女足依靠先农坛体校的资金托底,最少时,七八百万、女甲级别的年投入,每年都有球员离开。在 2024 年新赞助商出现以前,主教练于允一直把守住球队视为首要任务,“要坚持,还要保持最好成绩。成绩好了,才能引起关注。”
今年,拿到最大一笔投入、走出过去的资金困窘后,北京女足上下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有动力和决心。它也在学习如何变得更职业,扩充教练组团队,提升球员待遇,并重新开始售卖门票。这支球队的能力、决心与机遇,导向了暌违已久的冠军。
在此之前,职业化十年间,大连权健、江苏苏宁、武汉车谷江大,资金充裕的女足俱乐部已经相继站上过联赛冠军的历史舞台。女足仍是很难产生大众明星、也不够时髦的项目,被记住的几乎只有冠军。而即使是国家队的亚洲杯冠军,比赛过去后,“不足以带动女足项目在国内的热度。”一名从业多年的体育媒体人告诉《在场外》。
对女超联赛里的大部分球队而言,能吸引到的观众和赞助商始终有限。有球员告诉《在场外》,她想象中更好、更完整的联赛环境,就是观众更多。
2025 年开始的亚冠联赛还是为它们带来了更大的舞台和新的机会。国庆期间,武汉女足与奥克兰女足比赛的上座人数超过 3 万,这在过去的国内女足比赛中是不可想象的。就在明年,新的联赛冠军北京女足也将站上亚冠赛场。
时过境迁,拉开一个距离再看,北京女足的故事是许多“老派”的体育局女超队伍在联赛环境里的缩影──跟随市场的脚步投入重金,和先保证生存。它的夺冠是一场漫长的蓄力,也是一个关于如何在体制与市场的夹缝中,依靠“人”的力量生存下去的故事。
撰文丨毛思怡
编辑丨张钦

北京女足主教练于允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的。这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总是因宽大的办公桌和两排靠墙的柜子而稍显局促,墙上挂满女足大赛落场球衣,通常来自他带过的队员。桌柜台面上堆着五花八门的摆件,从去年到现在又添置了新的:北京女足两次夺冠的全队合影,和女超联赛冠军奖杯——摆在办公桌对面的文件柜上,一个他抬头就能看见的位置。

放在高处的冠军奖杯,实心的,特别沉
“领导给的任务就是联赛冠军。”于允在采访时开门见山。今年春节过后,北京市体育局局长于庆丰带着领导班子来了昆明,看望在海埂基地冬训的队伍,说希望女足成为三大球比赛的突破口。为了给她们鼓劲,每名队员收到一瓶安耐晒的防晒霜。
从去年开始,武汉女足对联赛冠军的“垄断”局面亟待其他球队打破。
2024 年初实行的女超新政对俱乐部国脚数量、年投入和球员年收入做出限制。武汉等少数俱乐部集中国脚、高薪外援的局面结束了,也带来一波人员流动,王珊珊、古雅沙等四五名重点队员在这一年从武汉回到北京。
再加上处在中间层、二十四五的球员,和从青年队补充的小将如王新灵、潘虹艳等,北京女足一线队的年龄层次分明,不再出现“人才断档”。尽管这年球队排在联赛第六,但结束了 18 年无冠的局面,收获足协杯冠军。
久违的冠军也许让市体育局看到了联赛夺冠的可能。领导们待在海埂基地的那几天,目标也定下来了,“大概需要多少经费,由我来汇报。领导觉得可行,自然会帮队伍找钱去。”于允说。
市体育局牵头为球队找到四家国企赞助,再加上主管部门先农坛体校的拨款,于允拿到自己成为主教练以来最大一笔投入,1000 多万。整个赛季,他时刻提醒自己,至少进入前三,对投入有个交代。
放在前些年,这笔钱可能不及争冠球队投入的一半。但现在,各队资金都有限的情况下,于允和领队盘算,想拿女超冠军,1000 多万也许足够了。
这一年北京女足球员们的薪水比往年提升了一倍左右。球队也变“专业”了,队内补充了全职的体能教练、数据分析和两名外籍按摩师——许多工作不用再由三名助理教练兼职。
但于允始终没有在队里提起过夺冠的任务,只模糊地表示“向最高目标冲击”。他坚持,一些自上而下的“包袱”只能由自己来消化。
也无须多言。球队陆续签下国脚张琳艳和三名外援后,“我们就感觉是最有可能拿冠军的一年。”球员彭雨潇说。为此需要更多的付出——联赛期间,一些年轻球员会主动跟着王珊珊加练,做些力量训练来维持被比赛消耗的肌肉,减小受伤概率。
为了给国家队比赛和全运会预赛让路,今年联赛赛程安排密集,有时一周双赛或八天三赛,留给球员恢复的时间很少。
上半赛季结束,北京女足排在第三,主力前锋穆科马和姚梦佳受伤,余下两名外援水平不足以出场。教练组不得不做出“补救”,临时决定引援,在夏季转会窗口签下从武汉女足离队的前锋特劳蕾。
“实话说,前几年没有投入,也没有这么大压力。别掉链子、别降级就行。”于允说。今年则不同,“干好了就继续,没完成就必须承担责任。”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也担忧过一种可能性:因为教练水平低,把一手好牌打坏了。
北京女足最磕磕绊绊的日子集中在下半赛季。从 7 月 19 日起,球队经历四场不胜,等到战胜山东女足后,只剩下最后五场比赛。有球迷喊出了“五连胜”的口号。“当时几乎全得赢下来,因为排在前面的辽宁和武汉总是比北京少赛两场。”一位北京女足球迷说,“没想到下一轮主场就输给上海。客场平河南后,大家都觉得冠军没戏了。”
北京电视台记者林琛也去了那场对阵河南的客场比赛。北京女足让二追三,最终在补时阶段因守门员失误被逼平,没能从保级队手上拿走三分。赛后,她看见于允一个人在板凳席上坐了许久,没敢上前采访。
等到球队围圈总结时,于允看上去还在跟自己较劲,“他当时说了句,‘我知道我就是没本事’之类的话。”林琛说。跟队报道北京女足的这三年,她第一次见于允的压力如此外露。
去年,于允说起过一个观点:女足项目本来就不受关注,再往后缩,就更看不到了。她觉得于允今年顶着压力接下夺冠任务的想法与之相似,“不往上冲就更没有资源。”
拼到最后,也许是看不见的运气起了作用。联赛最后五轮,辽宁、江苏、武汉等竞争冠军的有力对手轮番“掉链子”,纷纷不胜。倒数第二轮,北京赢下陕西之后,山东在读秒阶段绝平江苏,让江苏女足无缘提前锁定冠军,也把北京女足推进了决赛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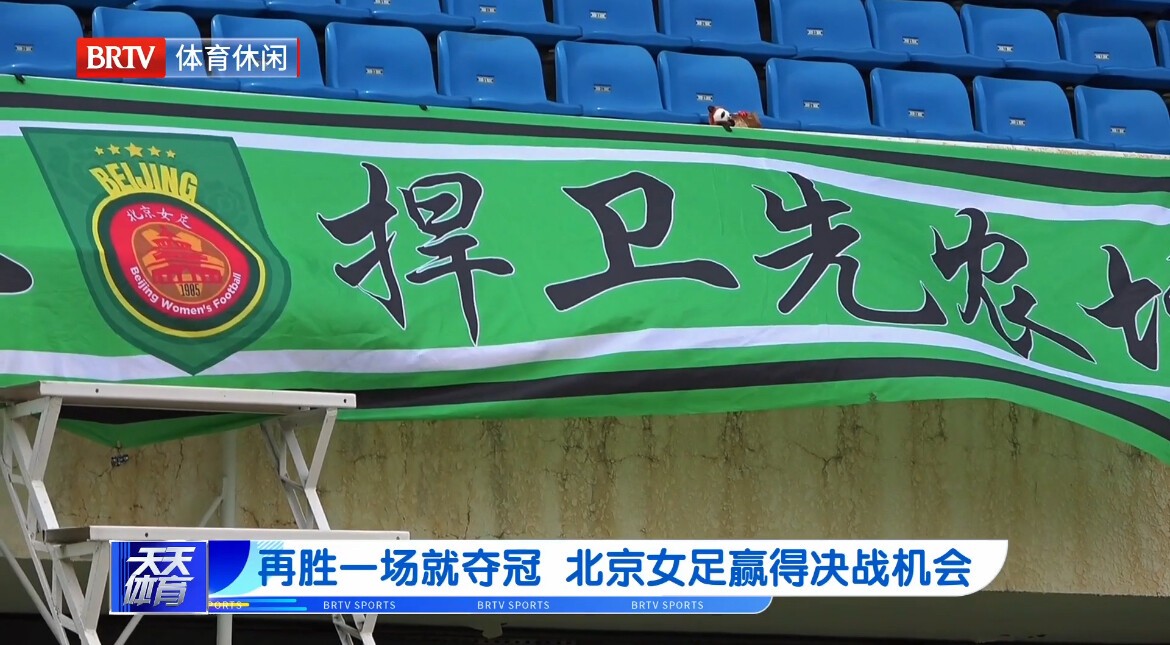
临近决赛,看台上挂起了“捍卫先农坛”的横幅
“没想到今年这么戏剧性。”于允后来说。一切几乎超出他的预期。在他原本的计划中,夺冠需要一个“过程”,今年尽力进入前三,明后两年持续投入,或许才能站到最高领奖台。
于允记得,决赛前两周,北京 U16 男足刚在主教练王长庆的带领下拿到全运会冠军。他看了那场比赛的转播,好友王长庆赛后相当激动,哭红了眼睛。“当时我很羡慕,我就想,我拿冠军了是不是也会这样?毕竟 20 多年没拿过联赛冠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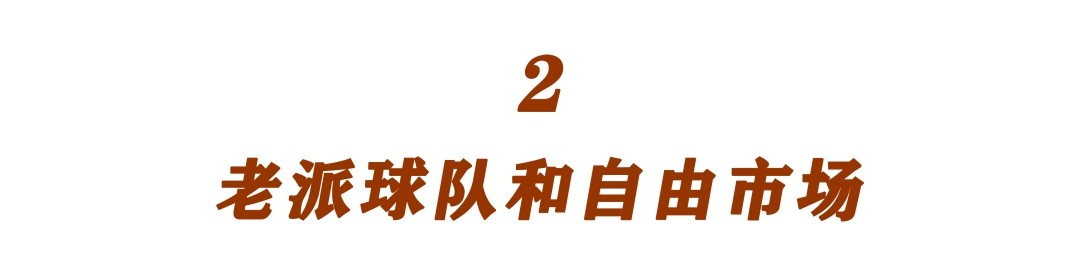
1985 年由先农坛体校组队成立的北京女足曾是国内比赛的冠军常客。它也是最早有企业冠名的女足球队。
中国女足在世界杯上拿到最好成绩的 1999 年,北京女足有多达 6 名球员入选国家队。那之后,球队新老交替、人才断档,又几度经历赞助商撤资,与冠军渐行渐远。
最近一次的赞助商撤资曾为北京女足带来持续 3 年的球员流失。在 2024 年得到北京雨虹修缮赞助之前,彭雨潇记得,那几年里翻看球队的合影,每个赛季都有人离开,“心里有种说不出来感觉。”
张晗理解一些球员离开的选择。失去赞助期间的北京女足只能靠体育局资金支撑,最困难的时候,年投入七八百万,和女甲队差不多,“提供不了和她们水平相匹配的待遇。”
国内女足转会市场的闸门在 2016 年被拉开。足协选择在这年开放俱乐部的球员转会交易,允许引进外援。“可以说是真正激活了女足职业化。”张晗说,“第一感觉,冲击。过去非正常的‘流动’,开始成为常态了。”
在这之前,女足球队基本以体制内运动队的形式存在,编制挂靠在各省市足协、足管中心下,各队之间极少有球员的流动。2015 年,女足联赛分级改制、开启职业化的同时,女超球队逐渐被推到俱乐部形式参赛的状态。各个省市加大力度成立女足俱乐部,如武汉车谷江大、上海盛丽、江苏苏宁等都在那两年间成立。
张晗在 2009 年加入北京女足,担任领队管理队务。他承认,女足转会刚放开时,对停留在专业队的北京女足而言很难适应。“各俱乐部开始招兵买马,各省市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现在我觉得特别正常,但当时我不这么想:我们把球员从十三四岁培养到进成年队、国家队,变成高水平球员,结果因为待遇不如其他俱乐部,让球员被别的省市签走了。刚开始很难接受。”
2016 年 11 月,投资方北控置业与先农坛体校签下 5 年合同,北京队也终于迎来转型,成为北京北控凤凰足球俱乐部。张晗回忆,尽管北京女足当时还没出现人员上的引进或流失,“但其实我们挺危险的。人家一直盯着我们队的三个国家队球员,古雅沙、张越和王晨。人家都想要,而且说待遇都能给到几十万年薪。”
国家队球员前所未有地向投入重金的俱乐部集中着。大连权健女足率先开启“集中国脚”模式,最多有过 9 名队员同时入选国家集训队。2019 年底,一度被称为“女足恒大”的权健女足解散后,武汉女足将这种模式推向极致,“替补席上坐的都是国家队员。”
后来 5 年里创造联赛五连冠记录的武汉女足成为了整个行业的领跑者,直到 2024 年女超新政后,“统治力”才有所下降,不过仍在强队行列。
限薪限投、“限制国脚过度集中”的新政发布前,足协征求过各队意见。“我一直觉得政策出太晚了。”于允说。他不欣赏集中资源的模式,不仅与他所看重的青训无关,也没推动联赛水平进步——像田忌赛马的故事一样,过去几年,很多球队不用主力阵容与武汉女足比赛。
流动是必要的,市场是重要的,“但得守规矩。”于允说。去年见面时他说起一件事,前两年有个队员接受了其他待遇更好的球队的邀请,与北京女足的俱乐部合同到期后,没和队伍商量,“说是自由身,直接就走掉了。但你是体制内的队员,你不能说走就走。女足和男足的市场逻辑不一样,男足没有编制。”
背后是体制问题。国内女足实行“双轨制”,以俱乐部形式参赛的同时,许多女超球队仍是由省市体育局保障运营的“体制内”队伍。
类似的流动在那几年里还是时有发生。“如果没有北控,可能北京女足会过得非常艰难。”张晗说。好景不长,2020 年底,北控以约定资金在 4 年内用尽为由,突然宣布撤资,“‘啪’地一下没有了。”张晗这样形容当时的感受。
社会赞助面上的投资从 2021 年开始归零,队员仅能拿到体制内工资,收入骤降。更棘手的是,全运会迫在眉睫。
张晗经常把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比作高考,“看教练组四年工作,最后能考多少分。”

采访当天,先农坛食堂大厅的大屏上放着全运会倒计时
停投正好卡在了布局四年、大考刚要开始的节点。北京女足失去几名主力队员,又被分在全运会预赛的“死亡之组”,被淘汰的可能远多过于能晋级。张晗回忆,当时于允成为主教练还没满两年,和他刚搭成新班子工作,二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还好,大多数队员宁愿放弃待遇也没离开。张晗感慨:“其实有俱乐部也给某几个队员开出了年薪几十万的条件,但她们跟我们聊完后就没走。”那一年,球队拼到联赛最后一轮才免于降级,但保住了全运会成绩,战胜广东女足后成功出线。赛后,他和于允走到场地另一端,忍不住相拥而泣。
而失去赞助商带来的尴尬没有结束。于允和张晗都想过办法。2022 年,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的第二天,于允联系了一圈认识的媒体记者,恳求报道队伍近况。那几年,两人在教练和领队的工作之外还要亲自为球队谈赞助,“基本谈不成”。想要留下或引进球员越来越困难。
从北控撤资到新赞助商出现之前的时间,被古雅沙称为北京女足经历的“阵痛期”。她也是 2021 年离开北京去武汉的球员之一,理由是想参加亚冠。两年后,王珊珊也因同样原因离开,北京女足流失了她在内的四名主力。
这些富有经验的球员的离开,让彭雨潇、马晓兰等 1999-2000 年间出生的球员从轮换迅速被推至主力位置。“珊珊姐在的话,整个队伍就不太一样。我们有安全感,敢做动作。”她们离开后,年轻球员必须开始独当一面。
2023 年北京女足有一个艰难的赛季。上半年,为节省经费,球队出征江油客战四川女足时只能带 18 名队员。5 月,主场 5:0 输给上海后,彭雨潇哭了,“本来没什么,姚梦佳拄着拐走过来安慰我说没事,她话没完我就哭了。”

2023赛季,北京女足前五个主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进球
江油客场结束的第二天,于允在朋友圈中分享了足球教练安切洛蒂自传中的两页纸:
“如果比赛的结果令人失望,那么运动员会开始觉得不再有那么强大的热情,他有可能开始质疑,过去那些日子他付出的努力是否值得。而教练应该忠于自己的想法,当然,这需要俱乐部的支持,一定不能左右摇摆。他需要坚定信心,决不妥协。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意识到,有那么一群球员正在他的领导下,一起证明他的选择和决定是对的。如果你很确定球员是站在你这一边的,那么这时候,你就需要把那些一定要做的事情进行到底。
如果这个群体顺利克服了这一系列的困难,那么他们会变得更加紧密,心理上更加强大,到那时,作为教练,你很清楚,每个球员都是那样团结,富有动力,还有决心。”
“我一直觉得北京队和别的球队不一样。张晗说。共同度过了“没钱的日子”,留下来的人之间并肩作战的情谊加深了。“今年所有人的目标、心思高度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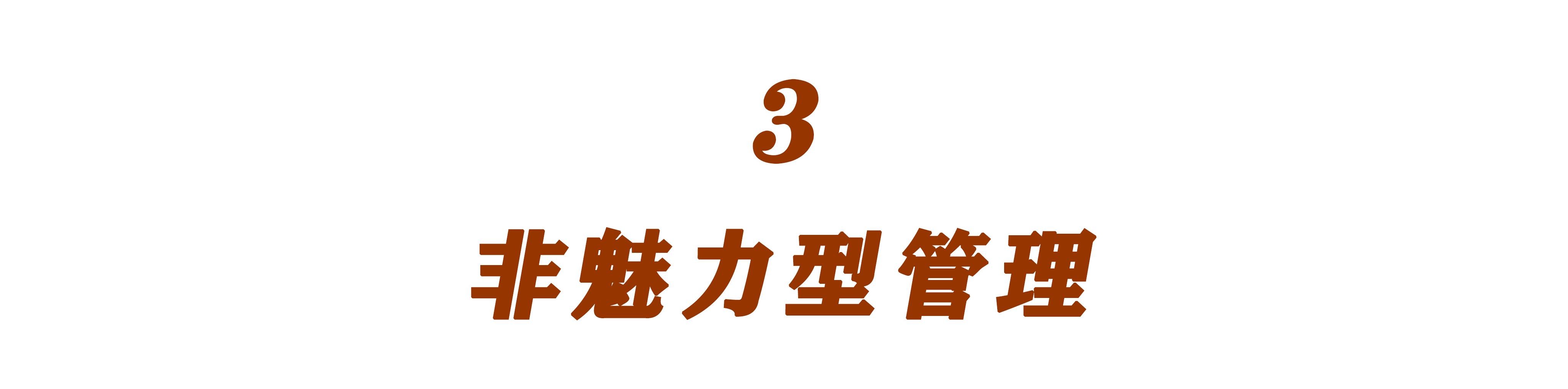
9 月 27 日,决赛前一天,北京女足的备战会上,于允先向全队读了一会日本国家队主帅森保一的书——《职业足球教练的工作 非魅力型管理的精髓》。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队员们说,于指经常在赛前念书。这天的内容是,什么是能够上场和无法上场的球员,达到哪些条件的球员会被选用。之后,教练组进入正题,开始对着视频分析决赛对手辽宁队的三外援,“也是名气不大、好用的类型。”林琛说。
最后是所有人都关心的奖金问题。于允说,帮你们去争取,能不能拿到看自己。“决赛当天,有队员告诉我辽宁队带着现金来的,拿冠军有几百万奖金。我说咱们不跟人比这个,先砸钱不是我的风格。”他后来承认,“如果当时说奖金是 1000 块乃至几百块,球员可能就没劲了,心理作用的影响是很大的。”
森保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自己是“管理型主教练”,只制定整体目标,具体的组织、训练安排由助教和后勤团队提出并执行,球员除完成既定任务外更需自我管理。有球迷把日本国家队类比成一家公司,金字塔顶端是主教练,助教、后勤团队是项目主管,球员是员工。这种管理风格强调团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林琛和北京队相处时有过类似的感受。于允一手带出的球员如彭雨潇、马晓兰、姚梦佳等人,都挺有“灵性”,场上动作大胆。
林琛印象里,彭雨潇这批“中生代”球员从没离开过北京队,也没有获得过比联赛冠军更大的荣誉。即使是从 13 岁起就来到北京队的老将古雅沙,也是去年才获得入队以来的第一个全国比赛冠军。决赛之前,“她们对胜利特别渴望。”

于允办公室里,2024足协杯夺冠的全队合影
而对张琳艳、王珊珊等荣誉满身的球员,她一直有个想法:已经拿过那么多次冠军,她们夺冠的动力在哪?
2022 年第一次转会北京之前,王珊珊在国脚云集的大连和武汉队内效力时都拿过女超冠军。“感觉不一样。”王珊珊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说,“比如在武汉队拿冠军的时候,身边都是国家队员,大家水平都高,没有太多拼搏感。”在北京队,有“老中青”三代球员,临近退役的她和古雅沙担着“传帮带”的责任,是年轻球员眼里的主心骨。一些球员告诉《在场外》:“有她们在场上,心里就踏实。”
她们决赛的对手是联赛中最年轻的球队——辽宁女足。这支球队去年刚获得第一届三大球运动会女子组的金牌,一半以上的球员不到 20 岁。“心态、比赛经验上不如我们老球员,在决赛赛场上可能太紧张。”王珊珊说。
决赛被认为是北京女足整个赛季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球队最终以 4:0 的成绩战胜辽宁女足。前锋赵瑜洁在这天完成了她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
加入北京女足前,赵瑜洁在丹麦克厄俱乐部效力,回国期间自己训练时受伤,被俱乐部提前一年解除合同。“当时就处在没合同的状况下,后来经纪人帮我联系到北京女足,它们愿意提供康复环境,帮我重新找回状态。”
她在去年 7 月回到赛场。于允执教青年队时就对这名上海球员印象深刻,接受采访时说过,“让她上场就是让她带节奏。”在美国、丹麦有过留洋经历的赵瑜洁,在他看来是“见过世面”的球员。
但在决赛之前,作为前锋的赵瑜洁已经一年半没有进球了。“听到进场歌曲,就开始紧张,站上球场草皮时都没缓解,只能一遍遍告诉自己专注眼前的事。”赵瑜洁说。
第 31 分钟,张琳艳在禁区内创造一粒点球,她没选择自己主罚,把机会交给了赵瑜洁。她后来解释,“来了一年半,拥有第一个进球对赵赵来说非常重要。”张琳艳也记得,今年足协杯,因为赵瑜洁罚丢点球,球队无缘决赛圈。“我相信她憋着一股劲。”
这枚点球打开了北京队的进球账户。像有某种魔力在球场上弥漫,4 分钟后,特劳蕾再次打进一球。“上半场咣咣 2:0 领先,感觉都要摸到奖杯了。”张晗兴奋地说。终场哨声将比分定格在 4:0 后,他大叫着冲进场内和队员们击掌相庆。
或许是等待的时间太过漫长,“我到现在还觉得今年的冠军像梦一样。”于允说。赛后,他像往常一样在教练席坐了会,没有第一时间站起来,后面才缓缓起身,含泪朝观众席挥了挥手。
采访时他说起一件事,队员们想在颁奖前把金色的训练服外套穿上,他说真正的冠军不见得非要穿这个,没让她们上楼拿。彭雨潇和他的想法相似,“只要能站在领奖台上,穿什么不重要。”过去接受采访时她说一直有个遗憾,从没听着《 We are the Champions 》和自己的球队一起站上领奖台。今年她终于伴着这首歌曲,看到了空中为北京女足洒落的彩带。

时隔23年,北京女足终于登上联赛冠军的领奖台]
张晗回忆,直到当晚他和于允、守门员教练姚健一块聊天时,三个人都还在兴奋。“我们把每个进球都捋了一遍,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可能是这辈子也不会抹去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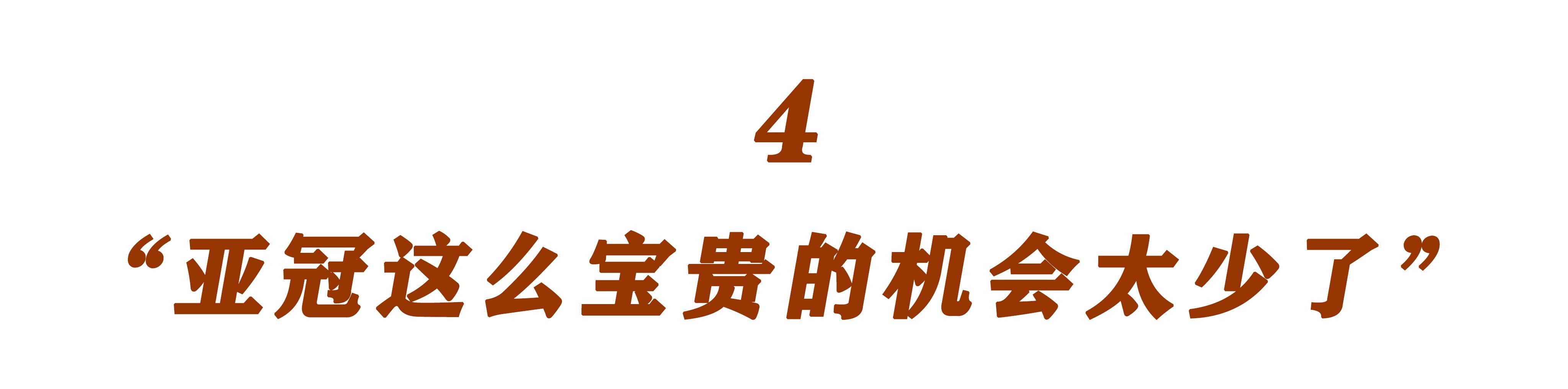
从今年四五月起,在海外踢球的女足球员纷纷结束合同,回归全运会资格所在省市的俱乐部,参加全运会预赛。
从北京女足转会法甲的王妍雯是为数不多还在海外踢球的女足球员。她的经纪人透露,好在球队和市体育局支持,在全运会备战上为她“开了绿灯”。
但从去年加盟第戎女足到现在,王妍雯一直处于“连轴转”的状态,“国家队比赛、法甲联赛、全运会预赛,她基本是全勤。”经纪人说,“疲劳是她整个赛季必须要面对和缓解的问题。”
今年,为了备战全运会正赛,北京女足在女超联赛结束后赴韩拉练,根据分组对手,选择首尔、仁川、水原三支不同水平的韩国球队进行了练习赛,力求拿回一枚奖牌。
面对同时身兼联赛任务的王妍雯,第戎俱乐部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王妍雯 10 月 12 日前往韩国报到,17 日返回法国准备第二天的联赛,19 日再回北京队。
“我觉得这样对队员来说太折腾了,也存在一定风险。”于允告诉《在场外》,“当时我就说,如果实在不行,我愿意再退一步,让王妍雯推迟一周归队,直接 19 日回来报到。更多还是要为运动员着想。”

王妍雯在法甲赛场
近年来欧洲女足蓬勃发展,逐渐与亚洲球队拉开距离,走出去接触海外先进的训练、比赛方式,被许多留洋女足球员视为提升个人实力和国家队水平的途径。为此甘于接受远低于国内的收入。
“王妍雯她们在国外挣的钱比国内都少。但她一直想留洋,我也要圆她这个梦。”在于允看来,虽然法甲前两三家俱乐部断层式领先,但整个联赛节奏快,能给球员带来提升。“她走的时候我跟她送了句话,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走出去看看是这个行业里大多数人的共识。张晗拿联赛的外援市场举例:塔比莎、特姆瓦、班达等球员曾代表过去国内女足俱乐部引进外援的最高水平,现在都已经去往美国或欧洲联赛。“可能也受到限薪政策的影响。”
这些“超级外援”退出后,国内女超联赛竞技水平、激烈程度有所下滑。今年联赛进球数前三的 5 名球员里,只有袁丛一个国内球员,但本土前锋和外援在进球数上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
一名女足经纪人也告诉《在场外》,现在球队引进外援有点像“刮彩”,便宜、好用是最现实的考量。这也被一些经纪人认为是联赛水平低的体现。圈子里的人仍在讨论一个问题,本质而言,是不是“还是谁有钱,谁买到好外援,谁拿(联赛)冠军?”
“还是得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像武汉参加亚冠那样的宝贵机会太少了。”张晗说。
武汉女足乘上了改制后的首届女足亚冠的机遇,夺得冠军。但也暴露出与海外俱乐部之间的差距——亚冠决赛中,武汉女足首发阵容平均年龄达到 29 岁,对手墨尔本城女足的首发平均年龄仅为 23 岁。中国女足已经多次出现后继乏人的尴尬,各俱乐部同样要面对这个难题。
有青训才意味着有自己的造血功能。在北京女足,情况也不容乐观。最大的困难是招生──北京踢球的女孩越来越少了。“近几年,据我所知,每年招生测试可能不到 100 个人。”张晗说。去年球队招募 2011、2012年龄段的小球员,准备组队,“从不到 100 人里头选小 30 人,和国内外那些优中选优的队伍比,差距就大了。”他希望球队这次夺冠能鼓励更多本地女孩踢球。
就在明年,北京女足也将迎来站上亚冠赛场的时刻。全队为之兴奋。她们都看过武汉女足的亚冠比赛,憧憬那样的舞台。

今年5月24日,武汉女足获得首届女足亚冠联赛冠军
就在国庆期间,许多球员刚看了武汉女足对阵奥克兰联,首届国际足联女足冠军杯的预选轮比赛,名字长到她们很难准确念出。张琳艳看得很感动,“球队下来后我就跟海燕姐她们说,我看到后面都想哭。这两年球队动荡,她们的每场比赛都是自己拼下来的,每走一步都是创造中国女子足球俱乐部的历史。”
转会到武汉的三年里,古雅沙也一度渴望踢亚冠。尽管她随队拿下联赛三连冠,但那三年,女足亚冠一直没有重启。
今年能在退役前和北京女足一起拿到联赛冠军对她来说意义重大。13 岁来北京,她在一线队待了快二十年,球队最好的成绩是第二、第三,始终与冠军擦肩而过。看着球员能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随队捧起冠军奖杯,她很羡慕,“但我也没有遗憾了。”
以 41 分占据联赛榜首的北京女足是近几年来积分最低的冠军。也被于允和张晗认为是近几年最有含金量的冠军——过去五年,除了 2020 和 2024 年,武汉总是提前几轮就锁定了冠军;今年最后两轮前,五六支球队都有拿冠军机会,是联赛竞争最激烈的一年,“谁都没放弃”。
球队内部也有一个共识:今年是比赛最好看的一年。各队都加大投入后,联赛水平有所提升。
但不知从哪传出联赛要从主客场制改成赛会制的消息。许多女超球员今年会在赛后主动给球迷签名,也对球迷说:“明年可能就签不到了。”
于允也听到传言,明年可能先进行第一轮赛会制,决出前六名和后六名,再分组进行主客场比赛。他常说,国家队水平和两点挂钩,联赛和青训。而女超重回赛会制对联赛发展是巨大的打击。
“我听说是因为有些队伍经费不足,但发展这么多年了,不能一支队伍经费不足就给改了。联赛取消主客场是历史的倒退,你看世界高水平联赛哪个是赛会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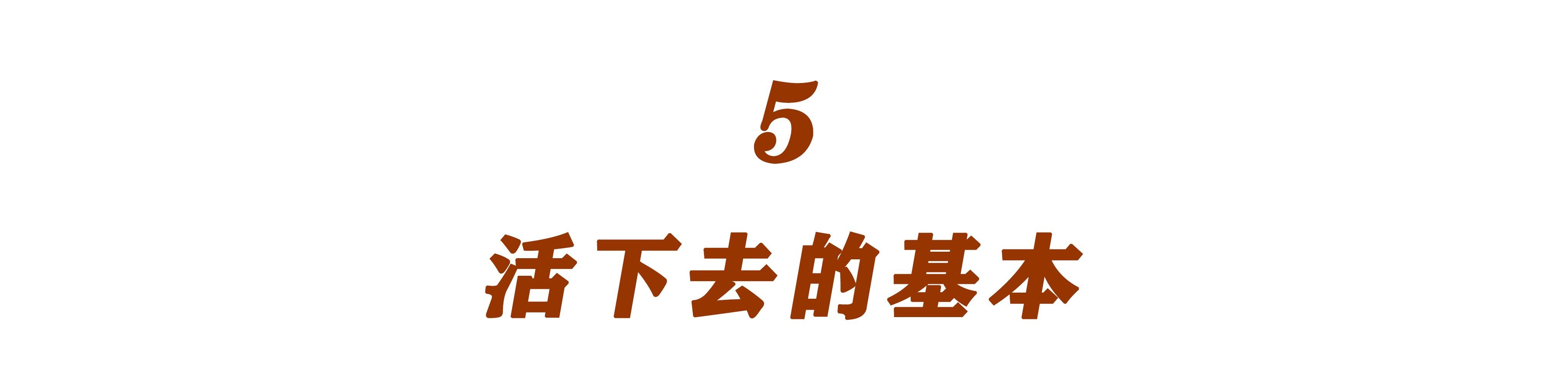
在于允办公桌的玻璃案板下,一直压着两张 2019 年出版的单向历,其中一张写着伊坂幸太郎《重力小丑》里的句子:“真正重要的东西就要明朗地表达出来。背负的东西越重,脚步就该越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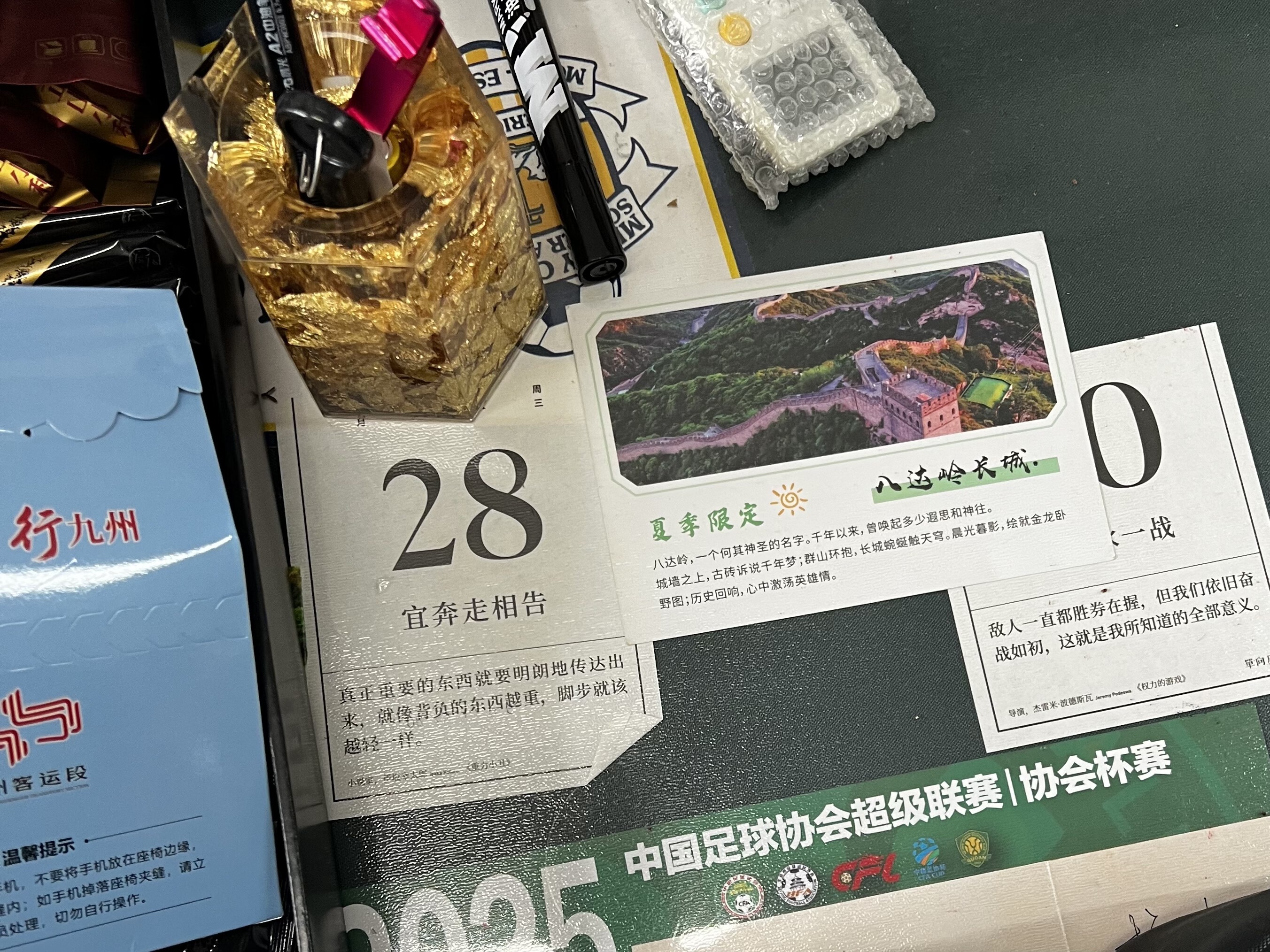
于允桌上的两张单向历
林琛觉得国内女足一直处在类似的环境里。“没有爆点。”她说,“国庆期间,WTT在北京那么大阵仗,好多人开开心心去看比赛。女足就没法比,它在自媒体上的传播,我觉得也不行,因为我在单位就做这些。”
她继续对《在场外》解释:“一些人说女篮和女足像,但女篮仍然有爆点。它有一些个性球员,像杨力维和杨舒予,她们会有自己固定的粉丝。而张子宇那种现象级的人物,即使是一个从来不懂女篮的人,只知道她这么高,打日本队时人家连球都摸不着,就觉得高兴,就传播开了。女足没有这样的现象,没有让圈外人帮忙参与传播的元素。始终是一种搅不动的感觉。”林琛承认自己有些难受,没有国际比赛的日子,绝大多数联赛场上的女足球员很难被外界看到。
夺冠是为数不多能打破沉寂的机会。今年女超联赛结束后,一家制作和发售球星卡的公司“FeverPaint”主动联系北京女足,合作发行了一套球星卡,印了张琳艳、王珊珊、古雅沙三名知名度较高的队员。
北京女足与外界的合作一直有限。它不算以俱乐部模式运作的队伍,没有总经理的职位,连赞助都需要靠领队和教练摸索如何去谈。张晗 2024 年前找过许多企业相谈赞助事宜,慢慢接受了女足队伍很难给赞助商带来实际利益的事实。
“最开始常跟赞助商说‘你们提需求,我们来完成’,后面发现这样沟通不对,人家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球队带来的宣传不如公司花钱请人弄。也有公司说得很直白,‘赞助你们能给我们什么权益吗?’我后来弄了个权益本,也叫‘菜单’,类似于一个权益表,专门拿给赞助商看,让他们看想要什么。”
但一切还是不了了之。直到“一名足球人”帮忙出面谈下北京雨虹修缮的冠名赞助,张晗意识到问题在于“我们女足俱乐部实在缺乏这种专业的商务人员”。
赞助金的不足或空白,缺口往往由体育局来填补。脱离体育局,80%的女足队伍活不下去,是于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体育局向来以全运会为重,对女足俱乐部来说,代表省市荣誉的全运会成绩多数时候比联赛成绩重要。
在球员们印象中,近两年来相对稳定的球队仍然是上海、武汉、长春在内的五六支球队,“我们也是今年刚好一点,有个别队伍还是挺困难。”彭雨潇说,今年球队投入变多,她觉得也和到了全运年有关。
一名其他队伍的女超球员向《在场外》回忆,主教练在赛前、训练前常常向她们强调:没有钱的情况下,我们能踢成这样已经很好了,我尽量少给压力,你们放开踢。“足球俱乐部不应该是这样的。”她说,“省里保留这支女足成年队,可能只是为了全运会。”
但全运会的女足成年组比赛也被于允认为是女足球队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在一个市场化不完全的领域,你就得需要这个杠杆的存在。”尽管今年有许多备战全运会的地方 U18 队伍参加女甲联赛,于允表示,很大可能,全运年结束后,这些过了全运会参赛组年龄的队伍就会消失。
今年过去后,时隔 23 年的冠军能为北京女足带来多少变化,现在还不好说。有球员觉得,冠军多少会让身价上涨,但据领队说,这仍然得看她们的赛场表现。
没有比赛和训练的时候,于允会去工人体育场看一场国安的比赛,“我最羡慕的就是国安,每场四五万人。”他也对今年武汉和奥克兰比赛的上座人数印象深刻,32318 人,这在过去国内女足俱乐部的比赛中是不可想象的。“实在是很大的进步。于允说。“比赛的级别毕竟不一样了。”
在女超联赛这片赛场上,观众一直不多。彭雨潇只在去山东客场比赛时体会过“在坐满 1 万人的球场里踢球”的感觉,“没人看你踢,和几万双眼睛看着你踢,就是不一样。”她想象中更好的联赛环境就是观众更多。

决赛当天颁奖时,球迷举起北京女足的手幅
除了山东女足,其他女超球队的观众人数常年在几十、几百到两三千间徘徊。
前两年,北京女足每场能有 1000-1500 个观众。队伍今年的上座率没有去年高,彭雨潇听说与安保条例变严格有关,先农坛体育场地点特殊,位于二环,“不允许聚集太多人。”
再加上,北京女足从今年开始实行买票进场,每周日比赛,卖票窗口在周四或周五就关了。有球迷投诉过门票窗口关闭太早的问题,没能解决,“好像说是如果买票的人太多,超过 1000 人就得一层一层往上报备,很麻烦。”
卖门票是于允的决定。他认为这多少能体现一支球队在一座城市里的价值。“不是说想靠卖门票发财或养活俱乐部,我觉得真要往职业化迈进,全免费也不像回事。咱尽可能的还是多干点职业的事儿吧。”
至于明年能不能继续保持今年的投入,于允暂时还没得到明确的答案。“但今年球员们也证明了,她们值得这些投入。”